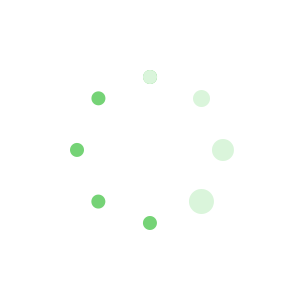美丽的哭泣(共3篇)
美丽的哭泣 篇1
父亲35岁时一场车祸让他永远离了我们, 母亲最终还是开始了和其他男人的约会。那些男人出现时动作招摇, 又紧张不安, 新理了发, 还散发出浓烈的香水味。可他们几乎没人能在我们家呆上过半天, 更没人来过两次。对我和妹妹来说, 他们只是我们开玩笑的话柄或捉弄的对象。
在妈妈的一次约会中, 对方在厨房里喝汽水, 太阳镜放在客厅, 我觉得试验一下镜架的强度很是不错, 结果镜架就像小嫩枝一样断了。后来, 那人返回客厅, 捡起碎眼镜, 装进口袋, 匆匆离开了。母亲几乎没说我什么, 但她似乎明白了14岁的我心里萦绕着的那份恶意。我看见了她暗暗抹着的眼泪。
几个月后, 妹妹来到我的房间。“妈妈又找了个男朋友。”她尖声地说。“有个大鼻子, 还说要来我们家吃晚饭。”
打父亲走后, 母亲还没有将其他男人邀请来吃晚饭。我似乎知道了这意味着什么。看来, 母亲这次对那个叫车又军的男人是认真的。
果然, 第二天晚上, 一个头发呈干草黑色、具有罗马雕塑般脸部线条的男人轻轻松松地站在我们的面前。他确实有个大鼻子。“这是车叔, ”母亲小心地向我们介绍, 手里还紧张地拧着条刷碗巾, “江南大修厂的车叔, 专修汽车。”
“我叫车又军。”他伸出手来, 我笨拙地握了握。在他那结了硬茧的钳工手里, 我的手又小又精致。“我们以前见过, ”他说, “你8岁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你, 那时, 你正躺在氧气罩里。”
是的, 8岁那年我患上了严重的假膜性喉炎, 呼吸困难, 不得不接受紧急气管切开术。我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一个星期。但我已记不起面前的这个男人是谁。
“我是你父亲的一个朋友。一天, 他搭我的工具车去医院, 我带给你一辆红色的救火车玩具。”
对人没了印象, 但提到那辆救火车, 我还是想起来了。救火车是钢做的, 橡胶轮子转起来快又平稳。我很喜欢这玩具, 有时候抱着它睡觉, 直至今天, 我仍能回忆起它贴在我脸上的冰冷感觉, 还有那亮漆发出的气味。……
不管我们怎么讨厌他, 那年春夏季, 车又军还是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家中了。一年后, 他不但每天晚上在我们家吃饭, 而且还跟母亲谈到了结婚。
我的怒火在燃烧。我很难想象这个男人占据父亲曾经拥有的位置。“我不会叫他爸爸的。”我对妹妹说。
“妈妈说, 我们可以叫他叔叔。”
“我也不会叫他叔叔。”我回答。我想, 一个陌生男人, 要想构建我们之间的亲密, 只能是梦。父亲虽然性情冷漠, 常发火, 但他在我们家的存在是那么强有力, 至今我还能感觉得到。
但车又军与母亲的关系却像春天的小草滋生起来。一个夏天的傍晚, 我玩完垒球回家, 当我走进前门时, 听到一支弗兰克·西那多的曲子。透过窗户, 我看到车又军和母亲在厨房中慢悠悠地跳舞。我过去从没看到过母亲和父亲在一起跳舞, 或者彼此情意绵绵。我一直等曲子结束才进了屋, 脸上当然是沮丧的表情。
“大修厂在人民路有份劳务活, 报酬是每小时6元。”车又军看到我, 显得很高兴, “要是你想做的话, 明天和我一块去。”
我一直在找份夏季工作。暑假打工的那种。犹豫了一下, 我还是说, “我很感兴趣。”
第二天早上7点钟, 他就开来那辆破旧的工具车, 将我接走。在清晨的阳光中, 我们开进了人民路。我被派去从拖车上搬卸轮胎, 当然跟他一起。
“怎么样?”下班后, 他问我。
“还好。”我告诉他, 累得不想多说, 但挣了48元钱, 对我这个一生之中第一次挣“外快”的穷小子来说, 我还是很感谢他为我提供了这次机会。
不久, 我们的心似乎贴近了许多。那时, 我正跟一个大学同学恋爱。“你妈妈说她很温柔, 谈谈她吧。”一天, 他对我说, 脸上当然还有赞许的味儿。这似乎激起了我心中的某样东西, 我也笑起来, 说, “好, 她的确相当温柔, 还善解人意。”
车又军几乎一辈子都住在那条又窄又小的小巷。一天, 母亲带我跟妹妹去他的家, 从邻居面前经过时, 他很骄傲地将我介绍给他的邻居们, “看, 某某大学的高材生, 学法律的。”话语虽轻, 却还是激起我心中的自豪, 让我的脚步似乎轻了许多。
大二那年, 车又军开始在星期六叫上我去大修厂帮帮忙, 无非是帮忙写写算算什么的。那时, 母亲下岗, 又要供我上学, 经济上不是太宽裕, 我没有拒绝他。后来, 他还教会了我修车, 说将来自己有了私家车, 出了故障也不需要另求人。工作时, 他将工具箱带在身边, 我就站在一旁学习他的手艺。
有时候, 车又军也带我去小吃店吃午饭。在那儿, 他似乎认识所有的人。一次, 他和一帮伙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, 他宣布我就是他所说的那个“大学里的巧师傅。”虽然那时候, 我刚刚学会怎样装卸轮胎。
大学毕业第二年的一天上午, 我告诉车又军, 由于预算削减, 我失去了司法局的固定工作。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:“我连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都保不住, 怎么还能找到愿做的事情呢?”他深思了片刻才开了口:“即使你找不到想干的工作, 也总能找到挣钱的事情。还想得起来第一次上人民路的事儿吗?”当然, 那一次, 48元, 为此我兴奋了好些天。
也就在那一天, 我意识到车又军在教我一种技能, 一种生存的技能。虽然, 他并没有外露自己的慈爱, 但他已用自己知道的独有的方式在默默地扮演着我的父亲。实际上, 那时, 他跟母亲还没有正式结婚。
后来, 我便进了车又军的大修厂。跟他一样, 做修理工, 工资是律师的两倍多。
有一天车又军得知我在发烧, 开车来到我们家, 带来一些水果。“你看起来不太好。”他说, 低头看着我。
“我觉得不太好。”
“我让你妈妈给你煮些鸡汤。还希望我给你带点别的什么吗?”
我脱口而出:“一个红色的救火车怎么样?”
他一时迷惑不解, 又突然笑了:“当然。”当他将我的工资放到床头柜上时, 我说:“谢谢, 爸爸。”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。
几星期后, 他打电话来说他要去墓地凭吊父母, 问我愿不愿一块去。他知道我父亲跟他的父母埋在同一墓区, 而自父亲的葬礼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。
我犹豫了一下, 说:“好吧。”
进了墓地大门, 车又军向我轻轻一点头, 就走向了他父母的墓。我看着他走开了, 迟迟疑疑地, 我也去寻找父亲的墓了。
找到父亲的墓后, 我呆呆地站立了很长时间, 直直地盯着刻在白色石头上面父亲简短一生的生卒年代。我想, 他早逝的最可怕的后果是, 我根本不了解他。他是谁?他爱我吗?
我站在墓前一动也不动, 后来车又军来了, 揽住了我的肩膀。“你父亲是个好人, ”他说, “他愿意为你做一切。”这句赞美的话打开了自父亲去世后我一直关闭的感情闸门。我开始抽泣起来, 他搂住了我。
回家的路上, 我们谁也没说话, 我很感谢他为我做的一切。他叫我一起去墓地, 让我恢复了自己并不知道的那正在消失的有关父亲的记忆和情感。而更重要的是在父亲的墓前, 他紧站在我身边, 让我知道了:他们两人都占据了我的心田。
然而, 三年后的夏天, 车又军出现背部剧烈疼痛。X射线发现他患了肺部肿瘤, 后来又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了骨头。我们惊慌失措。他一辈子没有得过重病。
但他却很坦然。面对所有的化验、可怕的报告单和化疗, 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或失去信心, 坚信医生能治愈他的病。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, 在向肺里送氧气的插管下面, 他露出笑容说:“别急, 事情总会有好结果的。”
我紧握住他的手, 我想像着孩提时他站在我病床旁的情景。
离开的时间到了。我俯下身深情地对他说:“我爱你, 爸爸。”车又军双眼迷蒙地看着我, 轻轻点着头, 紧握着我的手。那一丝微笑又浮上了脸。他心里清楚。
“再见, 爸爸。”我说, “明天见。”我走进冷气逼人的秋天暮色中, 强忍着泪水。
第二天下午, 车又军在睡梦中去世了。当我接到这噩耗时, 目瞪口呆。我再也不能听到他的声音了, 再也不能将工具放在他那有力的大手里了。
葬礼过后几个星期, 我去母亲的地下室找一把扳钳, 想替她更换漏水栓塞的垫圈。我打开了车又军的工具箱, 拿出扳钳, 但我没有返回, 而是紧紧地将扳钳抱在胸前。一股悲哀突袭而来, 我闭上眼睛, 想起我和车又军一起的许多情景, 深深感谢他和我一起度过那些时光。
母亲带着一篮换洗的衣服走下台阶。她看见我站在工具箱旁, 手里紧抓着扳钳。
“你为什么不把这些工具带回家?”她说, “你车叔他会乐意你拥有它们的。”
“车叔是个好人, 妈妈, 我很高兴你拥有了他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承认车又军在母亲生活中的重要性, 直到那时, 我才充分意识到母亲需要更早地听到我说出这些。在那堆工具旁, 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, 任无声的泪水滴落在扳钳上。
哭泣的麦秸 篇2
他叫阿商, 跟我青梅竹马。
那是一个柳絮曼舞, 夕阳金黄的黄昏, 他取出一枚戒指, 轻轻地套在我的中指上, 目光中透着深情:“阿诗, 这枚戒指, 我编织好久好久了, 一直没能有机会送给你, 又怕你不喜欢。今天, 我鼓足了勇气拿出来。现在, 我没钱买一支像样的戒指送给你, 只能送你这样的戒指, 等我以后有了钱, 再送你真的。”
那是一支用麦秸编织的戒指, 跟麦草一样的清纯, 带着一丝淡淡的幽香。
我无语, 惟有脸上挂两行清泪。好久好久, 我才幽幽地说:“这些话, 我等了好久好久, 现在终于等到了。阿商, 一枚麦秸戒指, 胜过千万枚金戒银戒, 我已足够。”
他轻拥我入怀, 眼里不知是因为幸福, 或是别的什么原因, 早已泪雾蒙蒙。
或许是太过激动, 也或许是太过幸福, 临去时, 竟连他塞进我衣袋里的东西也没发觉。
那是一封信。第二天, 我打开信封, 信笺上只有一句话:“阿诗, 我去了南方, 没别的心思, 我只想为你挣一只真的金戒指。”等跑到他家, 他早已坐上南下的火车。
孤独的日子里, 我摩挲着那枚麦秸戒指, 用它伴随我度过每一分钟。那枚戒指上, 有他的体温。思念, 也便浸润着我每日的生活。
每个星期, 我都会收到他一封信。信中, 他总说他在那边生活得很好, 说他每分钟都在想我, 说他挣的钱已快够买一枚戒指了。
最后一封信上, 这样写道:“阿诗, 昨天, 我在一家珠宝店里看中了一枚铂金钻戒, 它很像我送你的那枚麦秸戒指。等再过几个月, 我就带它回家。”
看完信, 我早已哭得一塌糊涂。这个可怜的男人, 其实, 他哪里懂我的心思。其实, 藏在桌子小木盒里的那枚麦秸戒指, 它早已成为我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, 它所散发出的那丝清纯, 那丝幽香, 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。
我把这些话都写在纸上, 寄给了他。
之后, 再没收到他的来信。两个星期、一个月、三个月……直到春节, 也没能等到他回家。
又是一个柳絮飘舞的日子。他突然回来了, 身边还多了一个女孩。他俩手挽着手。那女孩清清瘦瘦, 模样很俊。一副宽大的墨镜, 遮住了她一双一定很漂亮的眼睛。
那一瞬间, 迎接我的, 除了窒息, 还是窒息。我几乎已消失所有的思想。四周好冷好冷, 冷得我无法开口。
我眼光涣散地看着他挽着那女孩的手臂缓缓走过来, 听他仿佛来自天外的声音:“阿诗, 我回来了。这位是我的未婚妻可儿。”
我惟有无力地望他们一眼, 什么也没有说, 什么都不想说。
“阿诗, 这么久没给你写信, 是因为……我们在那边出了一点儿事。”他一边说一边看着可儿的眼神, “你知道的, 我们那个厂, 是跟化学品打交道的。一次实验中, 由于我的疏忽, 导致硫酸永远烧毁了可儿的眼睛。她是个善良的姑娘, 我不能让她一辈子一个人生活在黑暗中……”
之后, 我看到正抽泣的可儿, 一行清泪正从她墨镜的下沿流出。
怎么会是这样?我哭了。我紧紧地握住了可儿的手:“可儿, 原谅我。我不知道事情竟是这样。我祝你们幸福……”
在和煦的风中, 我伤心地看着他和可儿走了。我将泪水在风中飘成一滴滴晶莹的花瓣雨。
从此, 我将那枚麦秸戒指, 尘封在我的小木盒中。
可儿再次来到小村, 是在半年后。她仍然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, 却只身一人, 提一只黑色的旅行袋。她没有去阿商家。她说:“阿诗, 我只找你。”她缓缓地摘下墨镜, 露出的, 竟是一双流动着光泽的眼睛。
“你……你不是瞎子?”千言万语, 也难以表述我那时的惊奇与愤怒, “难道说, 你们一直都在合伙骗我?”可儿用点头回答。
“为什么, 难道就为了你们想在一起?”屈辱的泪, 也滑过我的脸颊, “阿商呢?阿商他在哪里?”
“他走了。”可儿不敢看我的眼神, “一年前, 他患上了肝癌。他一下子陷进了无边的黑暗, 对一切都不感兴趣, 烦, 闷, 百倍地思念你, 却又不敢给你写信。他不想让你经受痛苦和折磨。那是一个无风的黄昏, 他找到我, 含泪向我讲述了关于你们的故事, 包括那枚麦秸戒指。他说你善良柔弱, 于是求我帮他演一出戏。利用你的善良, 瞒过肝癌对他对你的打击。阿诗, 你能原谅我吗?”
看着这只黑色旅行袋, 似乎, 一种可怕的结局已浮在我的眼前。
“这么说, 阿商, 他、他……”我不敢往下想。
“是的, 我们组长他、他永远地走了……”可儿也哭了, 她拉开旅行袋, 里面, 是一只大红的骨灰盒, “阿诗, 你要坚强, 我们组长临走时说, 他还欠你一只戒指, 如果真有来生……”
水笔的哭泣 篇3
突然, 水笔转过头看见了它旁边朴素的尺子, 就带着轻蔑的神气说:“去!去!去!你长得太难看了, 怎么能和我住在一起呢?你看, 主人天天把我拿在手里, 生怕我掉在地上!你看, 我多重要啊!”
“尊敬的水笔女士, 你确实很美, 又很有用。可是我也有用, 主人要画线的时候就需要我帮忙啦。”
“难看的尺子, 主人才不稀罕你呢!”说着, 水笔激动地蹦了起来, 不小心从桌子上摔了个大跟头, “哎呦, 我的腰断啦!”话音刚落, 头上的两朵小花“啪”地掉在了地上, 笔芯也坏了。
这时, 主人来到了房间, 捡起地上的水笔, 看了看, 叹了口气, 说:“再好看的水笔, 要是坏了, 就没有用了!”说着, 主人把水笔扔进了垃圾桶里。
夜深了, 水笔在垃圾桶里呜呜地哭了起来:都是骄傲害了自己啊!